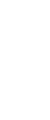返回 <<市场动态
4月数据点评:基本面持续分化,人口接近达峰
来源:明毅基金 发布时间:
A:供给约束和低基数影响,是全球近期通胀指标抬头的主要驱动因素。货币性因素固然是目前全球资产、商品、服务价格持续走高的先决条件,但通胀却已非内外部货币政策转向与否的决定性条件,决策评估的复杂度前所未有。
近期国内外主要数据方面,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4月国内CPI同比0.9%,前值0.4%,PPI同比6.8%,前值4.4%;PPI创年内新高的同时,接近6%的PPI-CPI增速缺口也创下自2017年2月以来的新高。5月12日,央行公布了四月金融统计数据,社融与M2增速不论同比还是环比均有明显趋缓,因其与引导货币名义增速向潜在经济增速回归的政策基调相一致,因此并未引发市场过度解读;然而北京时间当日晚,美国公布4月CPI数据,同比上涨4.2%,创2008年9月以来最大增幅,究其原因,既有近端的物价快速上涨因素,也有去年二季度疫情影响下的低基数因素。尽管此前美联储一再将通胀表述为“暂时性”的,但远高于3月且大大超出市场预期的通胀数据仍对市场情绪构成了较大冲击,并在当日美国股债市场都有立竿见影的反应。
实际上,对于通胀的担忧早有肇始。2020年一季度新冠疫情在全球传播以来:供给侧方面1)主要经济体为直接应对疫情注入天量货币流动性;2)上游资源国供给收缩、全球航运业运力削减;3)疫情的反复使既是资源供给国又是初级工业品制造装配国的南亚、南美等地一定程度被撕裂于全球供应体系之外;4)国内的供给侧改革、环保限产、碳达峰/碳中和等一系列政策平抑了潜在的(低端)供给弹性。需求侧方面,1)我国率先从疫情中恢复并制定了2021年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增长目标;2)发达经济体在疫苗帮助下逐步控制疫情并纷纷推出财政刺激计划,使得金融市场对未来与通胀密切相关的需求端驱动因素报以较高预期,并在实体端有效传导至下游消费和住房市场,进一步推升金融市场其对大宗产品的配置和交易热情。
不难看出,供给受限和低基数,是全球近期通胀指标抬头的主要驱动因素。一方面,低基数对同比通胀数据的放大效应有望于二季度内结束;然而另一方面,供给受限方面未来的演化路径却较难形成明确的一致性预期,其中疫情治理的客观能力要求与各国认知、动员、应对水平的主观差异构成了最重要的一组矛盾;此外,其它诸如病毒的变异、疫苗的迭代与覆盖率、大国间的非合作性因素等,都有可能从局部甚至整体角度抵消全球前期抗疫的成果,并致使供给受限和全球供应链体系向区域化的退化局面进一步向中下游传导。
此外我们更应进一步认识到,货币性因素固然是目前全球资产、商品、服务价格持续走高的先决条件,但通胀却已非内外部货币政策转向与否的决定性条件,决策评估的复杂度前所未有。未来,疫情因素、全球化的退化性因素、中国的内生变革因素,都将长期交织并作用于影响通胀的供给侧领域。例如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的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空间和传导渠道,扰动经济增速、生产率等变量,导致评估货币政策立场更为复杂。”相信不论中美,对后疫情时代的首次加息,都会空前慎重。
A:5月11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正式发布,显示全国总人口14.1亿人,2010年-2020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从七普数据来看,我国人口主要呈现少子化、老龄化、人口流动增加的趋势。“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增强生育包容性”,预示着鼓励生育的政策目标为大幅降低养育成本,使老百姓敢生敢育,缓解当前的少子老龄化挑战。
人口增速放缓态势明显,人口达峰争议再起。2010年-2020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相比2000年-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由于我国死亡率一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出生率。我国出生人口自2016年开始持续回落,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相比上一年少增265万人,也是仅高于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历史次低点;人口出生率仅8.50‰,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最低值。我国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3,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出生人数以及总和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我国育龄妇女基数连续8年持续下降;2)2018以来“二胎”红利逐渐释放;3)生育意愿降低有所降低。具体来看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是居住成本及养育成本高企共同导致的。首先,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全球最高的,2020年数据平均为13.2,其中深圳以48.1的房价收入比高居首位,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其次,随着大量年轻人涌入城市,城市拥有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但竞争激烈,推升了教育成本增长迅速,也极大程度压低了生育意愿。
我国老龄化趋势持续加深。老龄化方面,七普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占比为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有1.9亿人,占比达到13.5%,凸显我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压力。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划分标准,65岁人口占比超过7%意味着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占比超过14%意味着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按照IMF的预测,中国很可能将在2023年之前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从区域来看,几乎所有省份都步入了老龄社会,尤其是东北三省、四川、重庆以及长江中下游省份的老龄化程度尤其高,其中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高达17.5%,位居全国第一。生育率下降及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且生育率下降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规律性现象,因此老龄化过程难以放缓。从影响来看,养老相关产业将迎来新的机遇,例如养老院、养老地产;但人口老龄化加重社会养老负担,进一步制约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整体弊大于利。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提升,人口流动性持续增强。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3.89%,根据十四五规划,大概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即1400万人进城。城市化必然伴随流动人口的大量产生,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占到4.93亿人,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了将近70%。另一方面,人口持续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充分体现了“人聚财聚,人散财散”,东北人口和西部人口向南方发达地区聚集是非常明显的趋势。我国人口流动加快导致区域经济分化加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冲击更加剧烈,也是当前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非常惨淡的一个原因。
A:经济数据上,工业生产环比走弱,投资出现分化,消费不及预期,出口超预期。短贷收缩让金融数据下行再一次确认。风险上,需要警惕通胀的持续攀升对中下游产业链的挤压,近期市场的焦点在通胀和外需的持续性上。
工业生产环比走弱。以2019年的数据作为基期计算两年的复合增速,4月工业增加值复合增速为6.8%,强于上月的6.2%,但从环比和PMI数据来看,4月工业生产数据是走弱的,我们更倾向于走弱的观点。生产回落,部分原因是缺芯影响汽车、手机、计算机等产量,同时碳达峰背景下,黑色系的供给也有所走弱。
固定资产投资稳健恢复,结构性分化依旧显著。4月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小幅回升,基建投资增速出现小幅下滑。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当月复合增速分别为10.2%、3.4%(前值为7.8%、-0.3%),而基建投资(含电力)复合增速为3.8%(前值为5.8%)。我们在前期也提到,制造业投资是今年宏观层面,确定性比较强的主线之一,目前新兴市场国家疫情的反弹也让我国出口整体维持高位,支撑制造业投资的修复,当然目前来看制造业投资后续可能仍掣肘于出口和通胀。地产方面,销售、施工、新开工等数据延续了前期下滑的趋势,土地成交价款出现一定的反弹,我们推测这更多的可能是4月开始的集中供地制推升了土地单价的结果,而非地产投资的回暖。基建投资上,今年地方债发行明显偏慢,财政稳增长的积极性也不高。
消费仍不及预期。4月社零消费复合增速4.3%,上月的小幅回暖后又出现了下滑,主要是可选消费中的汽车消费下滑较多,其中3月汽车消费3930亿元,而4月该项仅为3585亿元。我们在前面也提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尚未恢复到疫情前同期水平时,消费的短期恢复是需要持续观察的,同时我们看到物价水平的持续攀升,也可能对居民消费端造成冲击,我们在美国四月的经济数据中发现了类似的迹象。
出口维持高景气度,其可持续性有待观察。以美元计价,4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32.3%,调整后增速为16.8%,进口同比增长43.1%,调整后增速为10.7%。分地区来看,4月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调整后出口增速均有一定回升,但对新兴经济体出口改善更为明显,对美国为17%,对欧盟为16%,对东盟为22%,对印度则大幅提升至21%,可能源自部分地区疫情反弹带来的对我国防疫物资的高需求。预计短期内海外经济修复释放较高需求仍将延续对我国出口的支撑作用,但新一轮疫情或将对出口造成扰动。
短贷收缩带动金融数据继续下行,社融顶点再次确认。4月社融增量、信贷增量分别为1.85、1.47亿元,而其存量增速分别为11.7%、12.7%(前值为12.3%、13.0%),收敛速度较市场预期略快。结构上来看,主要是短期贷款的快速收缩所致,表内中长期贷款、表外信贷、各类直接融资等基本符合预期。其中企业和居民短期贷款分别由3月的3748亿元、5242亿元收缩至-2147亿元、365亿元,我们猜测企业端主要是去年疫情期间企业经营现金流短缺下的贷款,与今年4月份集中到期有关,而3月中下旬严查经营贷的影响则在4月居民短期贷款上集中体现。
重要声明:本公众号所发布文章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或销售要约。基金有风险,投资请谨慎。 关于我们 明毅博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一家专注债券市场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公司成立于2012年,2014年成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